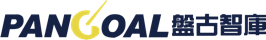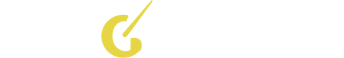中美关系:冲突亦或共赢? 听“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盘古智库怎么说

导语: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2月18日向国会递交了他上任以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报告中宣称,美国正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报告发布的前一日,盘古智库邀请“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举办新书分享会,与多位中美关系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
本文对参会专家在此次会议中分享的观点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2月18日向国会递交了他上任以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并在报告中宣称,美国正面对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报告发布的前一日,盘古智库邀请“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举办新书分享会,与多位中美关系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
本次分享会由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吕晶华主持,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原主任姚云竹,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战略室主任、《当代美国评论》执行主编樊吉社,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期刊编辑部副主任魏红霞,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纽约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张旭东,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郑玫,盘古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罗曦等与会并参与讨论。
会谈实录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与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
.jpg)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与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座谈
易鹏: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中共十九大于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美国新总统于今年年初上台并在11月8日实现访华。在新时代下,中美还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必有一战吗?
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很可能爆发冲突,这不仅事关历史,还事关人类命运。在之前的500年中,一共有16个有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案例。其中12个案例爆发了战争。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美两国离战争也更近了一步。本书的写作目的,一是要找出现在面临的危险性,二是要找出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解决方法。事实上,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
易鹏:中国在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没有扩张的基因,中国文化传统讲求“以和为贵”。随着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这种新变化,是否会降低陷入陷阱的可能,改变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并有一战的宿命?
艾利森:从中国军事战略上看,中国并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张和倾向。但这也反映了中国儒家的等级制度与世界观。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就像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如果大家都只关注这个,就容易陷入陷阱;但在宇宙中,太阳并不唯一,只是万千恒星中的一颗。
易鹏:国际社会需要公平,中国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有持续力,才有活力。
艾利森:所谓“平等”主要是在主权范畴,但是事实上,中国在国力上的大国地位不容忽视。相比于越南、韩国等邻国,中国在人口、GDP、军事等方面都是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获得了尊重和地位,还需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易鹏:在中美关系中,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毕竟中美有一战对中国不好,对美国不好,对全世界不好。你认为在实现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和谐共处的方面,智库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艾利森:智库需要推动解决朝核问题,促使金正恩停止核武器试验,这也是我个人的愿望。为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加强制裁,对朝鲜全面施压,另一方面需要盘古智库与其他智库合作,推动中美两国在这方面达成更深入的合作。
易鹏:解决朝核问题对中国、对东亚都很重要,但中国无力单独解决朝核问题。朝核问题处理得好,就可能推迟甚至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否则中美真可能陷入陷阱。但要解决问题,不仅中国要发挥作用,更多是美国要发挥作用。
艾利森:在朝核问题上,虽然特朗普和文在寅有过会面,但并没有取得很理想的效果。
易鹏:要解决朝核问题,需要换位思考,也就是朝鲜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以及核试验为什么能进行下去。我们要思考中、美、韩各方都做错了什么,从而导致了这个结果。各方需要合力找出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互相指责。
艾利森:在朝核问题上,过去20年各方表现都不好。各国专家应更积极地参与,推动两国通过新的协议,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主旨发言
格雷厄姆·艾利森
.jpg)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格雷厄姆·艾利森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者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为例:在当时的崛起大国雅典与守成大国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0多年,最终以斯巴达获胜告终,也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有广泛的体现。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因此,如果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这也是此次将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即此书的副标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当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竞争时,双方都面临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
尽管如此,中美注定一战中“注定”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出发,“国强必霸”不是中国发展的逻辑,这一点,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反复说过。习近平主席也曾多次在中美外交活动中提出通过尊重双方利益,互相尊重,合作共赢,防止战略误判,是可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
另外一方面,“修昔底德陷阱”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即便符合其中的假设条件,也不意味着理论就会自我实现,也不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中美关系会走上历史的老路。今天的中美关系本质上不同于一战前夕的德英关系。中美竞争的基本格局是一种过程式战略竞争,而非以直接利益冲突为主。针对中美关系中的可能性,一战与否,我们可以给出肯定和否定两个答案。如果按照老的套路解决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矛盾,我们会重复历史,重复结果;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即给出否定的答案,我们就需要学习历史,吸取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本次发言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25年中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是什么?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世界第一?一种观点是在十年后或者二十年后不远的将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问题的提出将引出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未来的25年里,中国崛起将对美国霸主地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阶段,中美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IMF的数据,2004年,中国GDP只有美国的20%;2014年,中国GDP略多于美国;2024年,预计中国GDP将比美国多40%。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经预言,中国的崛起会让美国陷入恐慌,因为还有另一个国家会像美国一样强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受到亚洲秩序的影响,而这个亚洲地区秩序则由中国主导。亚洲秩序将重塑美国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中国的领导人真的要取代美国重建国际秩序吗?李光耀的答案是肯定的。李光耀曾称中美两国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已经开始,而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区域大国,必要时也会展现力量。这个有着14亿人口、5000年历史的国家的力量展示给美国带来的影响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一个世代去适应的过程。
最后,我要谈的是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当前国际社会,或者说中美关系发展中最棘手的朝核问题会在将来的一年内让中美陷入战争吗?50年代的朝鲜战争已经先后让美国、中国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战争,那么历史将会重演吗?25%的可能性是特朗普政府对朝鲜采取军事制裁,阻止核试验的完成;15%的可能性是中美两国共同阻止朝核试验;剩下的可能性是朝鲜将完成核试验。人们可能认为,在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讨论中美开战有些“疯狂”。但我们需要记住,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都不想与对方开战,而最终爆发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中、美、韩等国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伤亡。现在,一个可能的假设是,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会率先向韩国发动攻击,由此造成的数万人伤亡会促使韩美进行反击,战争的不断扩大最终会将中国拖入,并导致我们担心的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爆发。
再举一个英德关系与一战爆发的例子。1900年的德国GDP约与英国持平,1914年的德国GDP比英国多25%,经济实力的增长促使德国建设大洋舰队,而英国此时已统治海洋上百年,制海权在某种意义上也已成为大英帝国的支柱。虽然英国与德国都无意与对方开战,但国家实力和战略的变化,配合上萨拉热窝的恐怖主义,最终导致一战爆发。
最后,《注定一战:中美两国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本书的主要意义在于激发人们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严肃讨论,而这一讨论必须是远远超越目前的范畴。
自由讨论环节
姚云竹
.jpg)
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原主任 姚云竹
艾利森教授认为中美两国可能因为朝鲜问题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的历史看,这种可能性很小,甚至低于10%。
首先,中美都是核大国,拥有现代化的军力,军事上的相互摧毁能力将抑制彼此冲突的风险。第二,中国参加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冷战背景下的中国是苏联社会主义集团和国际共运的一部分,这要求中国的政策不仅服务于中国利益,还要体现集团的利益;但冷战后与美国发生冲突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第三,尽管朝鲜半岛保留了某些冷战的特征,但中国致力于降低半岛冲突的风险。艾利森教授认为即使冷战结束了,朝鲜半岛的冷战仍在继续。确实,冷战后美日、美韩的军事同盟依然存在,朝鲜在冷战后依然感到很不安全,想成为一个核国家。但作为朝鲜邻国,中国并不想朝鲜拥核,中美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如果美国只是想实现无核化,而不是变更朝鲜政权、帮助韩国统一半岛,那么中美两国在半岛问题上就有共同利益,并会携手解决,而不是因为半岛问题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樊吉社
.jpg)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战略室主任、《当代美国评论》执行主编 樊吉社
第一,朝核问题毫无疑问影响了中朝关系的状态,并对中美关系产生冲击,但朝核问题将中美拖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真正有可能损害中美关系的是特朗普总统对中朝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以及他试图将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与中美关系中的其他议题挂钩。近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明确表示,希望中国采取超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外的行动对朝鲜施压。美国希望中国做的更多,却在外交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片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第二,朝核问题的未来有三个可能的发展趋势,其一是谈判,即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现在仍有谈判的可能以及希望,但机遇之窗越来越小;其二是延续当前僵局,朝鲜在外部压力之下获得可靠核导能力,成为类似印巴这样的事实核武装国家;其三是朝鲜半岛可能出现危机并迅速升级,从而升级成一场冲突,乃至全面战争。
第三,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有很多共同利益,诸如防止朝鲜进行核扩散以及避免朝鲜半岛生战生乱,但双方应对朝核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不同。中美处理朝核问题方式方法的区别类似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如果病人出现问题,中医通常认为是系统性问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不仅治标,更要治本,只有这样才能长远解决问题。对西医而言,如果病人有问题,通常采取靶向治疗,直接针对症状下药,如果需要甚至采取手术手段,西医重在治标。因此,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强调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而美国更喜欢就核谈核。朝鲜发展核导能力有其内生动力以及外部根源,只有综合治理,中西结合,对症下药,才有望彻底解决朝核危机。
李晨
.jpg)
盘古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李晨
非常欣赏艾利森教授近期提出的“应用历史”的概念,在分析和应对当下的大国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刚才提到的英德关系和朝鲜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作两点回应。
20世纪初的英德关系的经验教训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一些人简单认为,二十世纪初期,英德海上战略竞争导致了一战。实际情况是,英德海军的军备竞赛很激烈,在1909年左右达到高潮,但到1913年前后就终止了,因为德国已经发现,自己的海军无法赶上英国,而且还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应对陆上挑战,实际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认输。1914年七月危机爆发之时,英德海军还在基尔舰队周进行交流。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并不是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海上战略竞争并不一定导致大国战争。
朝鲜战争使中美迎头相撞为我们提供了警示,但中美双方有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美国学界反思朝鲜战争中也强调,1950年底中国参战后,美军在朝鲜遭遇的军事失败也包括较为典型的情报失误,主要原因是美国轻视中国的实力和决心,误判中国的意图,以及双方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中美双方对于朝鲜战争教训的吸取,在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体现出来。虽然美国是南越的盟友,中国是北越的盟友,但双方建立了有效的对话渠道,了解了彼此的关切和底线,避免了再次迎头相撞。这一危机管控也是美国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调整了对华的外交政策,并最终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的前提。上述经验教训在冷战后中美危机管控中也发挥了影响。当前,中美双方已经高度重视朝鲜半岛危机管控,明确彼此的利益诉求,防止误判和意外导致升级,并保持密切沟通,能够避免再度因为朝鲜半岛而迎头相撞。
达巍
.jpg)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达巍
现在要想阻止朝鲜完成其核导能力的推进只有两条路。一是由于朝鲜领导人在最近的火星15试验后,已经宣布完成了核导发展大业,那么或许朝鲜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停止进一步试验; 而美国又认为朝距离完全的能力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双方可以对朝鲜核导能力各自表述,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谈判。另一条便是朝鲜继续进行试验,最终导致美国对其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中美围绕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低,双方都不知道冲突的代价,因此会尽力避免。最后,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核技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响。艾利森教授研究中最近两次大国崛起未发生战争的案例都发生在核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核大国之间,崛起国与守成国虽然关系可能紧张,但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魏红霞
.jpg)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期刊编辑部副主任 魏红霞
我也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回顾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图片展现的历史很简单,著述书写的历史稍显复杂,而历史本身则复杂得多。因此,我们要分析历史事件具体发生的背景和条件,而不能简单地将当前的国际形势放到历史的框架中来看待。这里,我想从“例外论”的角度来探讨当今中美关系发展的愿景。一,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16个案例中,有4例成功地避免了陷入冲突与对抗,那么中美关系是否会成为第五例?二,美国标明自己是一个例外国家,这是否促使美国不会与崛起中的大国陷入战争?三,最近有人论述了中国的例外性,比如中国建设的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近代中国崛起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救的过程,那么中国做好准备挑战美国了吗?这个问题在美方看来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是在中国看来,中国还不具备挑战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主导地位的条件。四,当今这个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们的生活已经与科技密不可分,社交平台的普及应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利等都让这个时代成为历史的例外。上述这四个方面的例外情况可以让我们期待中美两国关系有望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历史的例外”。
罗曦
.jpg)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罗曦
根据艾利森教授新书的观点,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6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2例,那么最后4例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成功走向和平?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国家的因素,国家领导人因素,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因素等等。在中美大国关系中,我们需要明确战争与和平因素的比重,明确哪一个因素是中美关系的主导。
格雷厄姆·艾利森
朝鲜拥核非常危险,很可能使半岛陷入战争。由于不能确定朝鲜核武器的位置,不能确定朝鲜是否会对韩国等国使用核武器,朝鲜的核武器将成为不定时炸弹。中国也不想朝鲜拥有核武器,中美在半岛、核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问题是如何让朝鲜核试验停下来。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朝鲜继续核试,韩国进行核武装,中美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此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策有了新变化。特朗普不允许朝鲜拥核的强硬政策增强了半岛战争的危险性。虽然对朝制裁的加剧和朝鲜政策反弹的循环并不一定会引起“第二次朝鲜战争”,朝鲜问题在中美大关系中也只是一个小问题,但一战的爆发警惕我们小问题的不断累积会酿成大的冲突。
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朝核问题的发展方向除了朝鲜完成核试验和美国对朝采取军事制裁之外,还可以通过中美两国的沟通与合作来引导事态走向明朗。朝核问题既是中美关系中的新挑战,也是新机遇,如果应对得当,朝核问题可能会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的战略支点。可以说,中美两国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战略目标层面高度一致。但在应对方面,中美两国需要更好的合作,调整策略。
战争爆发是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在所有的16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共同点。有的战争案例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间,有的发生在两个具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国家间,还有的发生在有着类似的文化传统的国家间,所以我们不能将某一两个异同点或者因素作为判断国家间战争与否的标准。
不能指望这个时代成为“历史的例外”。所有的16个案例中,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国情,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而且都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中,当今社会独特的社会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上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个时代并不是历史的例外。至于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是否造就了这个时代的例外性,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文化是可以部分的独立于科技而存在的,文化的延续性保证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时代的延续性。
.jpg)
参会嘉宾合影